仿制药药效问题的真相:起源、痛点和治理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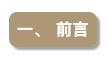
近日以上海市政协常委、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教授为代表的上海医学界代表在联名提案中反映某些集采药效果不稳定的问题,例如“血压不降、麻醉不睡、泻药不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也提交了《关于优化药品集中采购中存在问题的提案》,其中提到使用相同剂量的降压药,进口药可以将血压控制稳定,而使用集采药,患者血压难以控制至正常水平或波动较大。
从两份提案所反映的问题来看,所谓集采药的药效问题实质上是指集采中标的国产仿制药,其有效性评价的参比对象是相应的原研药。由于目前集采药物均是化学药品,本文内容只涉及化学药,不涉及生物药品(如抗体药、核酸药)。
作者作为曾经的医学工作者,对临床医生发现的某些国产仿制药的有效性问题早已有所耳闻,可能不少患者也有亲身感受。在医疗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作者对于京沪两地医生关爱患者、直面问题、积极探索的提案深表钦佩。
本文受到两份提案的启发而作,旨在简要分析仿制药有效性问题的由来、国内外有关法律制度与监管实践的比较,进而提出一些治理建议,希望能够为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理性思考的线索,支援各界人士在法治框架下共同推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的进步。

在现代医学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政府都要求所有药品在上市前都要经过完整的临床试验的检验,不论是原研药还是其仿制药。I-III期临床试验审批流程旷日持久且耗资巨大,导致即使是仿制药也价格不菲。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显著,高昂的药价让普通患者难以承受。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案——《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又称《Hatch-Waxman法案》)。这部法案彻底改变了仿制药的游戏规则,成为目前全球各国仿制药审批制度改革的蓝本。它允许仿制药厂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后,只需凭借药品的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数据,就能直接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简要申报(ANDA)。这相当于给仿制药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往市场的“快速通道”。
该法案通过后,美国仿制药行业瞬间被点燃。研发和申报的数量像火箭一样蹿升,药价应声而降,处方和销售量则一路飙升。首次仿制药的180天独享行政保护期让竞争进一步白热化。于是,围绕首仿权的争夺战愈演愈烈,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有的甚至不惜贿赂FDA官员。
1989年,美国仿制药厂巨头迈兰公司在申报仿制药ANDA时发现,其竞争对手的申报屡屡在晚于该公司的情况下捷足先登。公司董事长怀疑FDA审批过程存在偏袒,在向FDA申诉未果后,决定雇佣私人侦探调查。侦探通过翻查FDA官员的垃圾,发现了受贿和虚假申报的证据。迈兰公司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国会司法委员会。
经过美国司法部和FDA联合调查小组一年的调查,发现部分药厂为加快审批进程,采取了伪造临床数据、篡改实验结果、甚至直接修改原研药实验数据等不正当手段来让自己的仿制药品顺利通过FDA的审批。调查结果导致42名FDA官员和药企高管及10家公司被定罪并受到严惩,其中,FDA仿制药审查部主任及其两名幕僚因收受价值2.43万美元的贿赂被定罪判刑。
1989年的迈兰丑闻是全球仿制药行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暴露了仿制药审批中严重的申报数据舞弊问题,并促使包括FDA在内的全球各国药品管理部门对仿制药质量标准和数据透明度进行改革。
在迈兰事件之后,FDA还根据《Hatch-Waxman法案》逐步加强了对仿制药上市后监管的力度,例如,对仿制药的原料、生产与质量控制流程等方面进行定期实地检查,确保其符合美国药品生产的相关质量标准。
FDA的仿制药上市后审查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对前印度仿制药巨头Ranbaxy公司的处罚。FDA在稽查Ranbaxy公司Toansa工厂时发现,该公司员工在原辅料与原料药未达所需标准时,一再捏造检验数据以满足FDA的要求。2013年5月,Ranbaxy公司因销售掺假药物的罪名被美国司法部创纪录的处罚5亿美元。2014年FDA颁布了针对该公司产品的市场禁售令,同年,陷入困境的Ranbaxy公司被出售。一家成立于1961年的制药企业因数据造假、偷换原料和严重的质量控制失败,不体面的结束了其半世纪的奋斗史。
美国历史上,仿制药监管活动所发现的制药企业数据造假、偷换原料、不遵守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生产规范等不正当行为不是美国独有的,这些问题是全球各国药品监管部门普遍遭遇的严重挑战,中国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仿制药生产企业发生这些问题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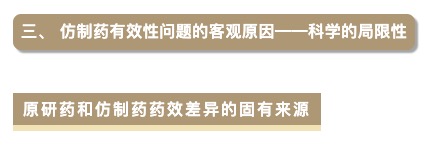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于2019年3月首次发布并实施了《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对原研药进行了定义,原研药品是指境内外首个获准上市,且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作为上市依据的药品。NMPA在2016年3月发布的《普通口服固体制剂参比制剂选择和确定指导原则》将仿制药定义为:与参比制剂具有相同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疗效的药品。
简单的说,原研药就是人类首次发现并用于医学治疗的新化学分子,通常原研药的有效成分化学分子都受到专利保护,不仅如此,以化合物专利为核心,原研药研发企业还会设置一系列的周边专利以保护他们的专有商业权利,比如分子晶型、制备方法、制剂技术、制剂辅料配方、用途(即适应症)、组合物、分析检测方法、中间体、前药和代谢物等等。从这些专利类型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制药技术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实现工业应用,可以说现代制药工业是一个国家整体制造业水平的指示器。
仿制药即指在原研药的专利过期后,其他制药企业根据已经公开的原研药技术资料进行的仿制。请注意是“仿制”而不是“复制”。原研药厂在公开技术换取专利保护的同时,基本上都会隐藏一些制药工艺中的诀窍(Know-How),将这些技巧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起来,例如中间体的制备技术、催化剂老化的判断方式、反应物的添加顺序等等,其商业策略是以公开最少限度的技术特征为代价换取专利保护。因此,仿制药厂不可能“拷贝不走样”的复制原研药厂的制药技术。由于仿制药在生产工艺、制剂技术、辅料选择、包装材料等方面可能与原研药存在差异,这导致仿制药在有效成分含量、杂质种类与含量、吸收率、血药浓度、保质期等方面可能与原研药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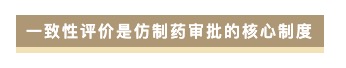
虽然仿制药存在与原研药的差异,但是客观的看,仿制药制度对全球医疗健康系统带来了许多益处。仿制药厂家因无需承担巨额研发成本和高研发失败率带来的沉没成本,其生产的仿制药往往以远低于原研药的价格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非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加了药品生产者的数量和产量,提高了药品的可及性;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竞争促进了药厂不断研发新药。
各国药品监管部门和医药从业者在几十年的仿制药生产与监管实践中,已经逐渐对仿制药的审批形成共识原则。鉴于仿制药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药物成分(API),两者的差异来源于生产工艺、制剂技术、辅料选择等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体现在药学指标(如药物的稳定性、溶出度等)和生物利用度(简单而言就是指摄入的药物能够达到血液循环的比率,主要指标包括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峰浓度(Cmax)和达峰时间(Tmax)等参数)等方面。
因此仿制药评价一般包括药学等效性评价(体外一致性)和生物等效性评价(体内一致性)。如果评价结果显示仿制药与原研药达到药学等效及生物等效,则认为仿制药与参比制剂(原研药)达到质量及疗效一致。由此可见,作为仿制药上市前审批的核心制度,一致性评价并不评价仿制药在患者身体上的真实疗效。

先哲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目前被全球广泛采用的一致性评价模式(药学等效和生物等效)虽然在理论上颇为周全,然而被一致性评价所采纳的检验方式毕竟只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模拟,不能保证其结果就是量产药品在人体上发生的真实情况,例如溶出度试验的结果可能不能如实反映缓释片剂在胃肠道的崩解和成分释放速度,稳定性加速试验无法模拟药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的温湿变化情形,生物等效性的有关试验是以健康人为试验对象,而真实世界的服药者为患者,受试药品的原料、辅料肯定与实际生产使用的物料批次不同等等。这些上市前一致性评价试验的局限性是短期内科学无法解决的。衡量仿制药的安全性、有效性最终还是要考察在用药患者身上产生的真实世界数据,即“药品上市后研究”。但是药品上市后研究只能指导对上市后发现问题的药品的监管,无法避免存在先天性的不为人知的缺陷的仿制药通过上市审批。

平心而论,我国的制药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差距。不仅内资药厂在研发实力上长期无力与国际制药巨头抗衡,即便是我国政府的药品监管部门也受限于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在管理实效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虽然国产仿制药品因价格优势长期占据主流份额,但是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和公共安全问题,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合适的时机启动解决国产仿制药存在的质量和疗效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加入WTO,我国制药工业部门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制药工业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加强自身技术实力,已经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2012年出台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针对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施行前批准的仿制药,在“十二五”期间要分期分批完成一致性评价。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44 号文)和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8号文)标志着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制度的正式启动。
我国仿制药监管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从一开始就大量借鉴了国外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短短十年间初步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监管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以及NMPA出台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分类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指导原则,囊括了从上市前审批、生产经营规范到上市后管理的全产品生命周期监管措施。
目前,我国仿制药监管主要的问题是“重评审、轻监管”。从行政执法状况来看,自2016年以来,NMPA将大量人力和行政资源用在了仿制药上市前的一致性评价体系建设上,这对我国制药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囿于资源不足,过审药品的上市后管理尚处于比较松散和低效的状态,制药业内多有“一致性评价”就是“一次性评价”的说法。
从立法技术上看,相关法律对于违反药品上市后管理制度的处罚力度不足。例如,《药品管理法》第七章“药品上市后管理”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是药品上市后管理的责任人,但是纵观整部《药品管理法》,对于违反第七章相关条款的处罚力度偏低,例如该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存在未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变更进行备案或者报告、未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未按照规定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或者上市后评价的情形,仅仅给予“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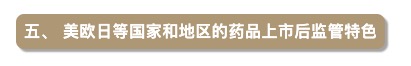
全球各国政府的药品监管理念、原则正逐渐趋同,但具体措施各具特色。下文中各国和地区的药品上市后监管措施仅为对比中国监管措施后的列举,不代表其总体概括情况。
1、美国FDA是负责该国市场上仿制药上市后管理的主要机构,其特色管理措施包括:
不良反应监测:FDA通过 MedWatch 系统收集药品的不良反应报告,包括仿制药。所有药品生产商都需报告任何严重的不良事件,任何医师或个人均有直接向MedWatch提交和查看不良反应数据的权限。虽然医师和个人报告的数据可能缺乏药品和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通过大数据技术,MedWatch依然具有重要的预警和参考作用。
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监测:FDA要求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药在生物等效性方面一致,这一标准会持续监督。FDA定期审查仿制药的质量标准,确保其与原研药相符。
强制性药品标签更新:对于发现有安全性问题的仿制药,FDA要求生产商更新药品标签,告知患者和医生潜在风险。
2、欧洲的仿制药监管由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各国的药品监管机构共同负责,其特色措施包括:
药物警戒(Pharmacovigilance):EMA通过 EudraVigilance 系统监控仿制药的安全性。所有药品生产商必须报告药品的不良反应和任何新的安全性问题。
上市后再评价:EMA要求对所有上市药品,包括仿制药,进行定期的上市后再评估(Post-Marketing Evaluation)。对于存在安全性问题的仿制药,EMA会评估其风险与益处,并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市场准入。
生物等效性与比较试验:对于新仿制药,EMA要求进行临床试验以验证其与原研药的生物等效性。对于已经批准的仿制药,EMA也会定期审查其生物等效性数据。
3、日本的仿制药上市后管理由厚生劳动省和日本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共同承担。其特色管理措施包括:
新药再审查制度:日本对所有新上市药品只授予临时销售许可,在上市后进行再审查,通过设立再审查期,收集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重新评估药品的获益与风险。
药品再评价制度:再评价的对象是所有已上市药品,包括老药。随着医学和药理学的发展,对过去批准的药品每隔5年进行重新评估,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与最新信息保持一致。
社会共治:日本的药品上市后管理不仅依赖政府监管,还强调药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例如,风险管理计划(RMP)在药品获批后在 PMDA 的网站上进行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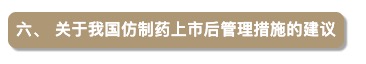
(一) 加强信息透明
信息透明在药品监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增强了公众对药品监管体系的信任,还通过促进药品监管的公正性、提升监管合规、加强药品安全性和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目前,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尚未出台针对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和上市后研究的信息公开要求。作者认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作为药品上市后安全性、有效性的责任主体,应当公开自行开展的上述两项工作的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 构建社会共治治理格局
药品上市后监管涉及多个环节和主体,药品使用者动辄数以百万计,仅靠政府监管部门难以全面覆盖。社会共治鼓励临床医护人员、药品销售企业、公共卫生工作者和公众参与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监督,如通过研究数据上报、质询、举报等方式,增强公众对药品安全的关注和参与度,形成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率,能够促使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更加主动地履行药品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不良反应监测等责任。
(三) 定期开展药品上市后再评价
仿制药的有效性问题既可能来源于一致性评价的局限性,也可能来源于人为的不正当行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用真实世界数据的上市后再评价才是检验仿制药有效性的最有力手段。严格的上市后再评价也可以震慑那些通过数据造假“侥幸”过审的企业。如药品因经不起上市后再评价而退市,不仅让为通过一致性评价而花费的成本沉没,还可能因此被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并受到惩罚。总之,绝不能让“一致性评价”真的成为“一次性评价”。
(四) 加大对未遵守生产管理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
上文已论述,制药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不是物料与原研药一致就一定能造出好的仿制药。一个不太严谨的类比是对标烹饪技术,使用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的菜肴可能有云泥之别。
某些人可能有这样的心理,先用符合规范的物料和工艺生产出供审批用途的药品,在过审后,只要原料、原辅料没有安全性的问题,就可以在物料、生产工艺上“降本增效”。
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对于假药、劣药的法律定义,上述情况生产出来的药品并不一定能被归入假药、劣药并以触犯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追究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
但是仿制药是中国重要的药品品种,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健康。对于进入集采范围的仿制药,其有效性还关乎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对任何导致药品有效性问题的不正当行为的处罚都应当具备足够的威慑力。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药品生产企业最高处以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笔者认为这样的罚款力度难以有效阻吓潜在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大型药企时,可能显得不够“痛”。在此建议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等方面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呼吁相关监管机构及立法机关加强法律责任体系建设,探索提高罚款额度、丰富处罚手段,并通过强化执法力度,以增强法律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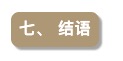
自2016年起,NMPA全面启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明确要求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逐步完善一致性评价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确保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一致性评价制度显著提升了国产仿制药的整体质量。
但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一致性评价不能保证仿制药上市后的有效性。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都是造成仿制药有效性问题的原因。对此,仿制药的上市后管理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加强信息透明、构建社会共治治理格局、定期开展药品上市后再评价以及加大对未遵守生产管理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是提升我国仿制药上市后管理水平的关键措施。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作者与任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制药企业不存在利益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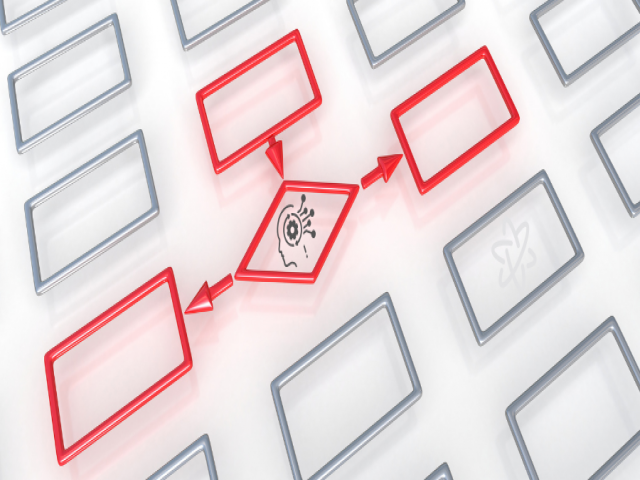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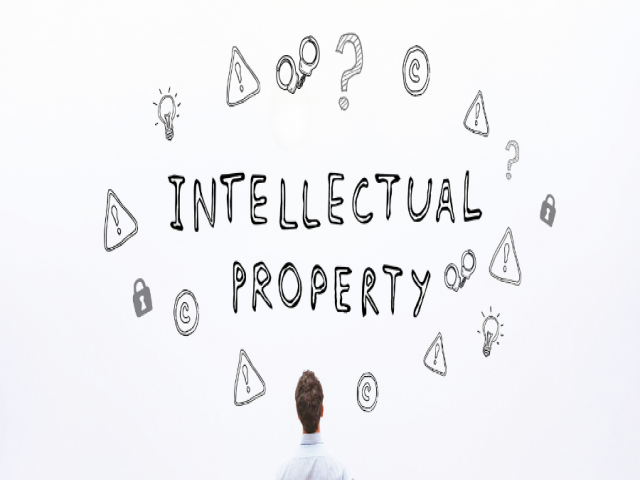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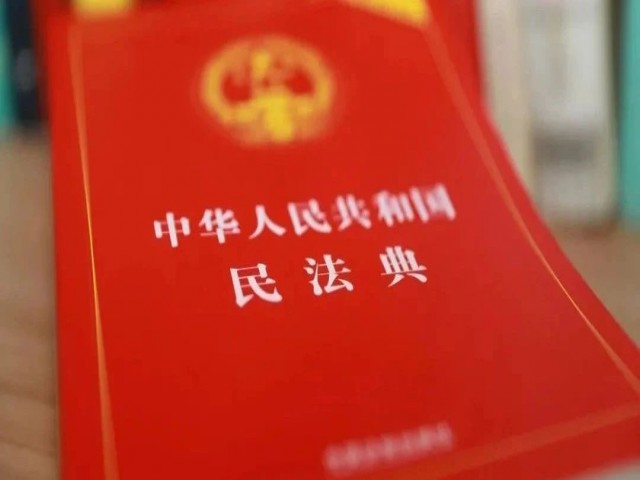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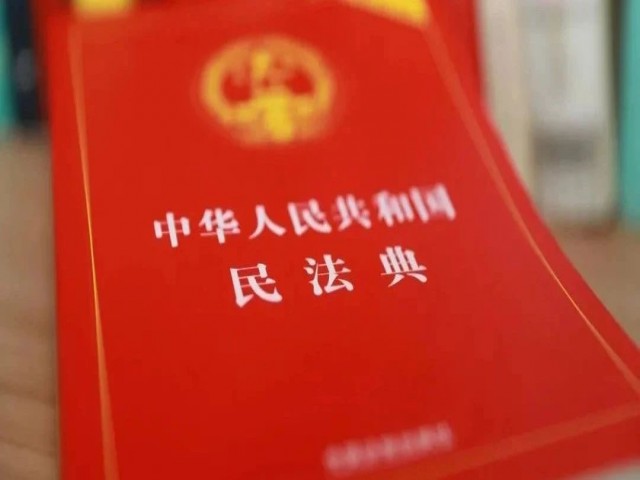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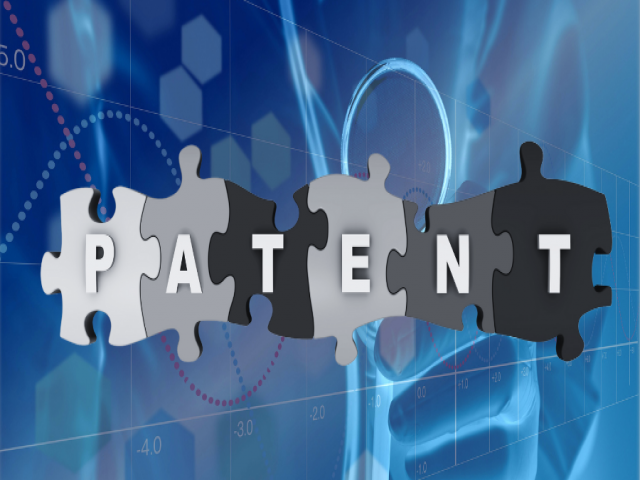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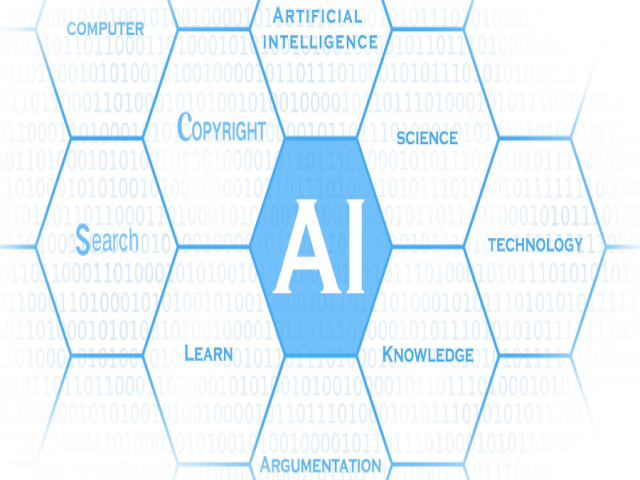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