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速评
7月最后一天,最高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称为“《解释二》”),笔者注意到,解释二在最高法院早在2月17日已经讨论通过,直至实施(9月1日)前一个月才公布,其中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涟漪,耐人寻味。
《解释二》在《民法典》实施、《解释一》发布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回应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中一些常见和突出的问题。其目的一如既往是统一法律适用、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和谐劳动关系。
《解释二》主要在稳定劳动关系角度发力,涉及以下几个内容:
1.劳动合同稳定化:强调用人单位不得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义务,细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合同”的认定标准。
2.社会保险刚性:明确任何形式的“约定不缴社保”均无效,劳动者因此解除合同的,可以要求经济补偿。
3.混同用工与挂靠责任:强化承包人、被挂靠人及关联企业的连带责任,避免推诿。
4.竞业限制:仅在劳动者接触商业秘密或保密事项时有效,过度限制部分无效。
5.双倍工资例外:用人单位可在证明劳动者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订立合同时,免于支付二倍工资。
6.服务期与违约责任:对劳动者未完成服务期提前离职的情况,法院可判令赔偿损失。
7.涉外用工:对外国人劳动关系、外国企业代表机构的劳动争议给出规则。
但是,站在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法律关系的角度衡量,《解释二》无疑并未回应外界对《劳动合同法》生效以来,僵硬而充满争议的劳动纠纷问题的重大关切,并做出有效的回应。相反,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拿掉了用人单位剩余的不多“救命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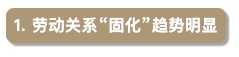
《解释二》继续强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延长劳动合同期限累计达到一年以上,延长期限届满的;(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劳动合同期满后自动续延,续延期限届满的;(3)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用人单位变换劳动合同订立主体,但继续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合同期限届满的;(4)以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规避行为再次订立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的情形,均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在这个条款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第(4)项,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规避行为”均构成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由此,可以想见未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将成为绝大多数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上海从今年年初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的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的认定口径的变化,与此次公示的最高院讨论通过《解释二》的时间节点的关系,似乎也可以一窥究竟。
强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强调劳动关系的长期性,的确有利于稳定就业,但也大大增加了用人单位在市场环境变化下灵活调整人力结构的难度。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产业结构快速调整背景下,企业用工弹性被削弱,风险成本上升。是否最终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新人,甚至在技术革新的名义下,使用机器代替劳动者,显然并不在此次《解释二》出台的考量范围之内。

《解释二》第19条规定“任何承诺不缴纳社保均无效”使得灵活用工、平台用工中常见的“劳务费模式”风险显著加大。企业必须全面纳入社保缴纳体系,否则将面临劳动者解除合同与经济补偿的双重压力。

《解释二》第18条是一条比较拗口的条款:“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终止可以继续履行的劳动合同,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终止决定作出后至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前一日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用人单位、劳动者对于劳动合同解除、终止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规定与现在的司法实践有显著变化。比如上海的《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引起劳动争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或人民法院裁决撤消企业原决定,并且双方恢复劳动关系的,企业应当支付劳动者在调解、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其标准为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劳动者本人的月平均工资乘以停发月数。双方都有责任的,根据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计算的期限上,《解释二》是从解除终止决定之日起与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规定的“劳动者在争议期间”的差异;二是计算基数以《解释二》规定的“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与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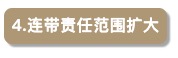
《解释二》的前三条对转包、分包、挂靠以及关联公司之间的用工责任做了规范,解释倾向于确认实际用工方与关联企业的连带责任。这对集团公司、产业链企业而言,意味着合规要求和用工风险集中放大,企业间“风险隔离”机制削弱。

与针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的固化相反,《解释二》对竞业限制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弱化了企业通过竞业条款保护商业秘密的效果。对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需要更多依赖内部管理和技术措施,而非仅仅依靠合同条款。当然,这个变化也是国际上的大趋势,通过限制人才流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变化具有进步的意义。

《解释二》对“特殊待遇”做了扩张,承认劳动者在未履行服务期义务及享受特殊待遇而未履行对应义务时需承担赔偿责任,用人单位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包括培训投资等特殊待遇在内的利益。但这里的特殊待遇是否可以解释为除了专项培训以外的待遇,有待司法实践的落实。
整体而言,《解释二》以“稳定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为核心价值导向,强调就业稳定优先于用工灵活。对用人单位而言,明确责任边界,降低部分企业被动承担过度责任的风险;允许在部分情形下追索劳动者违约赔偿。
但与此同时,《解释二》进一步压缩灵活用工空间,使企业在人力资源调整上的弹性减弱,尤其在市场环境快速波动时,将面临更大的人力成本和合规风险。对新经济形势下的灵活用工模式(如平台经济、共享用工、自由职业者)回应不足,传统劳动关系框架仍然主导解释体系,未来可能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实际情况产生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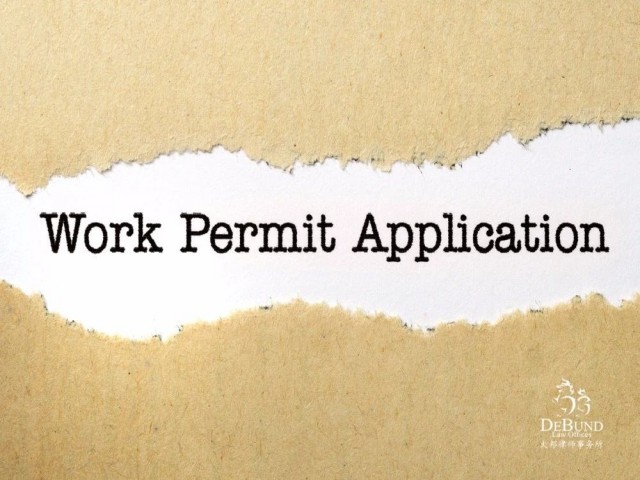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